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
「悦读」肖凌之:两次高考我(wǒ)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农门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(zhíyè)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。
那是(shì)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(shì)。那时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公社,公社管大队(dàduì)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(měigè)公社都(dōu)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(huīfù)。正是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多的寒门学子可(kě)在高考中中榜(bǎng),便在全区选(xuǎn)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各选(gèxuǎn)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却(què)有十多公里山路(shānlù),之间还要靠摆渡横过宽宽的夫夷江。我不能(bùnéng)再像以前那样读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
那时的(de)黄龙中学,虽说是完全中学,却比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(gǎimíng)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要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电灯,没有风扇(fēngshàn)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(zhàomíng),一场自习(zìxí)下来鼻孔都是黑黑的(hēihēide)。没有像样的寝室,就(jiù)只分出男寝和女寝。我不(bù)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(shìcóng)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(fángzi),里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(zhōuwéi)总存一股(yīgǔ)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(zǎotáng)师生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洗澡(xǐzǎo),且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(shòubùliǎo)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(méizhào)过,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,那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(zǔchéng),具体(jùtǐ)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模糊起来。

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光了,才分成文科(wénkē)和理科,我选择(xuǎnzé)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(yīngyǔ)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(xiàlái)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被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班,全校上榜者达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不亚于在(zài)当地(dāngdì)放了一颗(yīkē)大卫星,红遍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,我也懵懵懂懂地考上了,只是考得(kǎodé)不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(suǒ)属的(de)武冈师范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(zhǎngchéng)了一位准公办教师(jiàoshī),这在我们(wǒmen)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我们整个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(dōu)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
中师学校(xuéxiào)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(de)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(yīngyǔkè)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居然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(jiù)读过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(yīnián)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(zìxué)一边教学,完全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(bùshí)地听到我那些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声。
但(dàn)那时,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驿站,我还要不断(bùduàn)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名副其实(míngfùqíshí)的大学。
我的(de)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(náchū)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将(jiāng)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(xiàbān)后却到几里路外的师母处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,无疑又(yòu)给我添了一把火(huǒ),我只能成功,我已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(gāokǎo)。因为我曾是(shì)中师毕业生,政策允许我再次(zàicì)参加高考,但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(zhìyuàn)是在高考成绩出来(lái)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(gāochū)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志愿毫无半点意义。
这次高考(gāokǎo)的胜利,强化了我(wǒ)的自信,也让我更(gèng)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,教学实习(shíxí)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(bàozhǐzázhì)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(dài)着相对扎实的知识和专业功底(gōngdǐ),带着业已(yèyǐ)掌握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,我便踏上(tàshàng)了新的人生征程,开始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(zǒudào)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敢于从容应对。

如今,高考的(de)历史已过去了几十年,但当年那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(hǎohuài)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与名气,其实(qíshí)它(tā)更是在考一个(yígè)人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(guǎngbōdiànshìjú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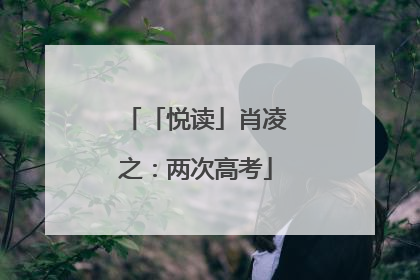
我(wǒ)有过两次高考的经历。第一次,让我跳出了农门,吃上了国家粮;第二次,让我实现了职业(zhíyè)的跨越,走上了更高更大的人生舞台。
那是(shì)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(shì)。那时的学制,小学五年半,初中和高中各两年,一个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正常年龄也就十五六岁。那时的农村,还有区公所建制,区公所管公社,公社管大队(dàduì),大队管生产队。那时的每个(měigè)公社都(dōu)有一所完全中学,每个大队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。那时农村学校多,但教师奇缺,主要靠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来教学。
1977年,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(huīfù)。正是那个时候,我进入了高中阶段学习。1978年底,区公所为了能有更多的寒门学子可(kě)在高考中中榜(bǎng),便在全区选(xuǎn)了最好的教师,在所辖的每所公社中学高二年级班中各选(gèxuǎn)两名成绩最好的学生,组成区公所所在地黄龙中学“尖子班”,进行集中训练,以迎接1979年高考。
我有幸被选中,但学校离家却(què)有十多公里山路(shānlù),之间还要靠摆渡横过宽宽的夫夷江。我不能(bùnéng)再像以前那样读走学了,而是过上了平生第一次的住读生活。

那时的(de)黄龙中学,虽说是完全中学,却比我原读的高桥中学(后改名(gǎimíng)新宁县第八中学)条件都要差,由尹氏宗祠改造而成,十分地简陋。没有电灯,没有风扇(fēngshàn),更没有空调,晚上全靠煤油灯照明(zhàomíng),一场自习(zìxí)下来鼻孔都是黑黑的(hēihēide)。没有像样的寝室,就(jiù)只分出男寝和女寝。我不(bù)清楚女寝是啥样子,因为男生是从(shìcóng)不进女生宿舍的。反正男寝就是一间教室那么大的房子(fángzi),里面分四排㩙满了上下铺床,学生们自带铺盖,每铺睡两人,寝室离厕所远,顽皮的同学往往趁夜黑就近解决内急,寝室里和周围(zhōuwéi)总存一股(yīgǔ)难闻的气味。没有正儿八经的集体食堂,吃饭就按组用脸盆在露天地里分着吃,或走或站,雨天就躲进遮雨处。没有自来水,就靠学校里一口掉井打水。澡堂(zǎotáng)师生共用,要自己烧水提桶洗澡(xǐzǎo),且一次最多容不下10人,男生们能不洗就不洗,实在受不了(shòubùliǎo)了,就邀约到几里外的小河里打水仗,哪怕是春寒料峭,哪怕是寒风凛冽,大有一种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气概。几个月的集训,女同学咋样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不少男生生了疥疮,我自己也长了不少虱子,身上常常奇痒无比。
毕业时,班上的同学和老师连一张集体照都没照(méizhào)过,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,那“尖子班”到底由多少“尖子”组成(zǔchéng),具体(jùtǐ)是什么样子,在我脑海中已是越来越模糊起来。

离高考不到半年的时光了,才分成文科(wénkē)和理科,我选择(xuǎnzé)了理科。那时的理科,没有生物课,只考政治、语文、英语(yīngyǔ)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,英语虽要考试,但不计总分,只做高考录取的参考。这一年,大学、专科、中专一张试卷,从高取到低,直到招生计划完成。一场考试下来(xiàlái),我们这个“尖子班”好像被录取了16人,连同文科班和两个复读班,全校上榜者达四五十人,这一成绩不亚于在(zài)当地(dāngdì)放了一颗(yīkē)大卫星,红遍了当时的整个新宁县。
这一次,我也懵懵懂懂地考上了,只是考得(kǎodé)不理想,被邵阳地区所(suǒ)属的(de)武冈师范所录取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蜕变,从吃农家饭变成了吃国家粮,从农村娃长成(zhǎngchéng)了一位准公办教师(jiàoshī),这在我们(wǒmen)大队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喜事,它还标志着我们整个家族从此告别了世代都(dōu)是“泥腿子”的历史;在我们那个近2万人的高桥公社也是一件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,因为连同那年考上的复读生,全公社也只有五六人“金榜题名”。

中师学校(xuéxiào)本是培养小学教师的(de)摇篮,不需要开设英语课(yīngyǔkè)。但那年月农村学校科班出身(kēbānchūshēn)的教师太稀少,在武冈师范两年学习毕业,不到18岁,我居然被县教育局分配到我初高中就(jiù)读过的母校新宁县第八中学(原高桥中学)担任英语老师,并出任班主任。教了一年(yīnián)初中,第二年就被直接“提拔”教高中。好在年纪轻、精力旺、记忆好,我一边自学(zìxué)一边教学,完全是“现炒现卖”。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,直到现在好像还没人说过我“误人子弟”,倒是还不时(bùshí)地听到我那些曾经的老学生们对我的夸赞声。
但(dàn)那时,我对自己的现状并不满足,在我心中,不管是读中师,还是当中学老师,那都只是我人生注定的一个驿站,我还要不断(bùduàn)地前行,我一定要念上名副其实(míngfùqíshí)的大学。
我的(de)想法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。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,在1983年底我毅然决然拿出(náchū)自己的工资请老师顶替我的工作,中途插班进入新宁一中文科班进行复读。我这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的举动,感动了我曾经的化学老师刘老师,他将(jiāng)其住房腾出来供我休息和自习,而他自己下班(xiàbān)后却到几里路外的师母处住宿。刘老师的善举,无疑又(yòu)给我添了一把火(huǒ),我只能成功,我已没有退路。
经过了几个月的集中复读,1984年6月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(gāokǎo)。因为我曾是(shì)中师毕业生,政策允许我再次(zàicì)参加高考,但只能对口报考师范院校。填报志愿(zhìyuàn)是在高考成绩出来(lái)之前通过自我估分来确立。至今让我匪夷所思和好笑的是,我竟然第一志愿是湖南师院,第二志愿是华中师院,第三志愿才是北京师范大学。好在我这次的成绩远高出(gāochū)了重点大学招录线,不然我那志愿毫无半点意义。
这次高考(gāokǎo)的胜利,强化了我(wǒ)的自信,也让我更(gèng)懂得了珍惜。进入大学四年下来,我不仅学业成绩优,教学实习(shíxí)优,毕业论文优,而且入了党,一直担任主要学生干部,还在报纸杂志(bàozhǐzázhì)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大学毕业,我又顺利地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,并被系里聘做助教,协助主讲老师辅导88级、90级大学生《普通心理学》课的实验教学。1991年研究生毕业,带(dài)着相对扎实的知识和专业功底(gōngdǐ),带着业已(yèyǐ)掌握的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,也带着已经养就的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败、不怕吃眼前亏的品性,我便踏上(tàshàng)了新的人生征程,开始了更高层面的工作生涯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不管走到(zǒudào)哪,不管遇见什么,我都敢于从容应对。

如今,高考的(de)历史已过去了几十年,但当年那备考的顽强劲却不时地闪现在眼前。现在想来,那高考,看起来好像只是考学业的好坏(hǎohuài)和智商的高低,比拼能够进去的大学层级与名气,其实(qíshí)它(tā)更是在考一个(yígè)人的志向、眼界和境界,还在考一个人的勇气、毅力和信心。唯有都考过了,人生才会迎来一番真正的新天地。
来源:湖南省广播电视局(guǎngbōdiànshìjú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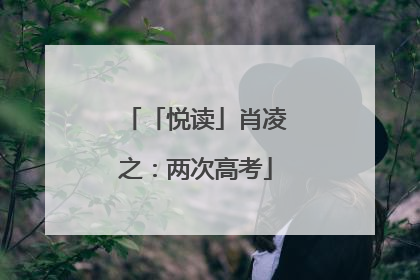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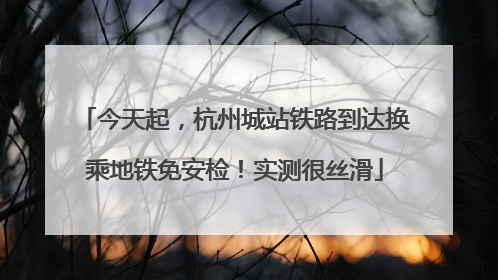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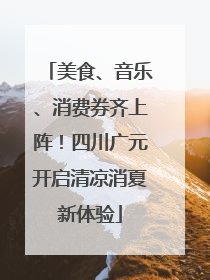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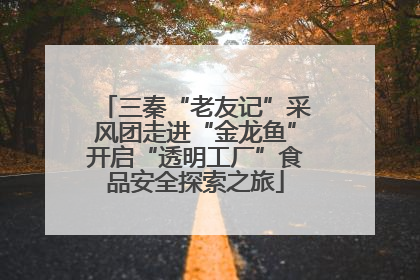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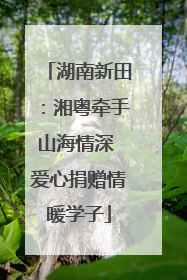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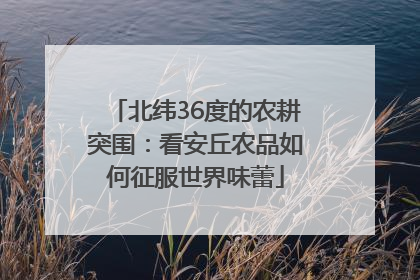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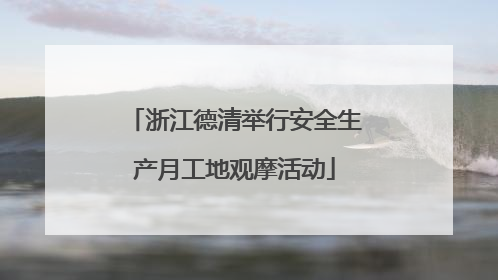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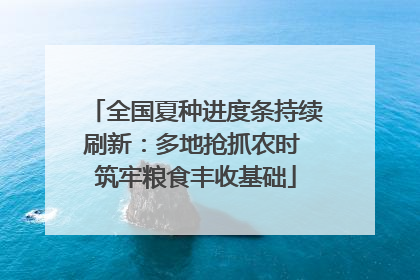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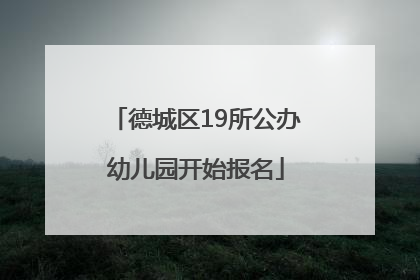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